《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读后
编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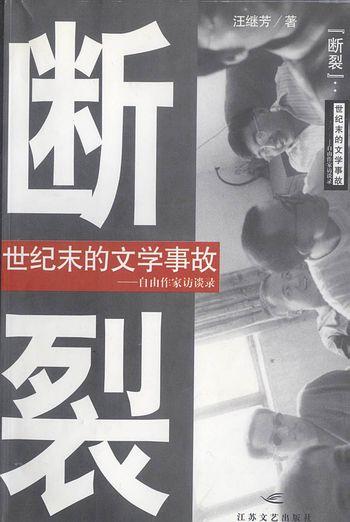
说实话如果不是论文我肯定不会找到这本书,甚至也不会去了解什么晚生代、新生代,命运让我们相连,这是一种神秘,我只能归之于此。
韩东说:“现在大家都把穷归于文学,这不对,你穷是因为你整天不干活,钱要去挣才有,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用稿费来养活自己也是不现实的。”“你不能因为穷就让穷侵蚀了你的灵魂。其实我们已经从文学那儿得到了我们该得到的东西。”追求自由就必须甘于困苦,但自由又成为断裂乃至他们写作的基点,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单纯。朱文认为文坛的恶意和质疑之所以在他那里不能成立是因为“标准”的差异,他们强调的是个体价值、个人主义,而这在当时的环境里是不可能被承认的。面对断裂,每个参与者的反应也不同:吴晨俊的后悔犹疑、顾前的游戏心态、朱朱的超然不关心结果、李小山的相对冷静肯定、韩东朱文的激烈坚持……行为造成的结果已经超越发起者的把控(实际上他们也并不在意它的走向,至少他们声称如此),尤其在大众传媒与消费主义勃然崛起的时代,走形变样是必然的,一代人与他们前代之间的隔膜也因此非但没有打破,而且变得更深。其实,分歧在行为尚在进行中就已经变得复杂,在问卷发表之后,韩东直言,“体制内”的一群也与“体制外”的一群也多少产生了破裂。时隔多年以后再度回看,每个人对此的态度又各有变化:鲁羊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隐隐透露出过于当年轻易介入的后悔;韩东在顽强坚持的同时也逐渐陷入某种难言的迷茫。而前两天的作代会上,当年参加断裂的大批作家却不少已经皈依他们曾反抗的“一切即存体制和秩序”,并且依靠着这些东西生活得很好。种种颇富意味的表现,令这个事件变得愈发暧昧。
冷静下来看待的话,断裂的价值或许从未得到确切的评估,无论是既存的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著作,都只是匆匆带过,不愿多说。但从当下的写作者以及文学环境中,似乎多少可以推敲出其中的某些端倪。记得朱岳在一条广播里提及对韩东的看法,他似乎将后者视为创作上的榜样。这种情况早已发生在韩东的同代人身上,顾前说与韩东的相处形成某种压力——他在玩,而韩东在写,这种无形的影响以某种难以直接把握的形式在那批被某些研究者称为“南京青年作家”的群体中弥漫着。这群人对朱文韩东的敬佩,对他们写作的喜爱有着很强的一致性,同时,韩东朱文也很欣赏自己朋友的作品。面对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容易形成直观的“刻板印象”——圈子、小集体,但却往往没能意识到这种过于轻易获得的印象实际上消解了潜在的其他因素。作品里的朱文,粗俗不堪,被视为流氓写作;韩东同样书写性,并将之作为主要对象。按他们的看法,现存的文学观念实在过于肤浅也过于道德化。文学是否应该被道德“俘获”,这无疑是个难以回答的宏大命题。但是否道德低下的书写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就是不合法的写作?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不应再轻易作出论断。忘了是不是郜元宝说的,朱文写作的隐藏着巨大的虚无和悲哀,朱文也说“虚无不是彼岸,恰恰是起点。不虚无我觉得倒是奇怪的,对人生的这种感受,虚无肯定是基本的,除非你这个人是很容易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温情来麻痹的。”确实,生存在一个价值失效理想被嘲弄的时代,尤其在经过特殊事件的风波之后,理想主义消失给这些作家带来的虚无和对世界的紧张如果真的不存在才是可疑的。
华东师大的一篇硕论指出:断裂的真正结果是断而未裂,这批作家已经刻印上了八十年代的印记,无法抹除,他们的困厄和不适应也根源于此。这篇文章的作者在写作中仍然持一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观念,虽然克制,但字里行间仍然显露出对这批作者的否定。相反,复旦的一篇博论作者却更清晰地为我们勾画出这个群体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场域”(既是抽象意义上又是具体实际地理上)的,在他的论述和对材料的补充中,能更好地看出这批“同人性质”的群体所持有的文学立场和观念(尽管它更多是韩东和朱文引领主导的)。这位研究者提醒我们,用道德标准来审视这群作家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否定基于道德标准的判断,对此毫不关心,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真的形成了一种可以用于建构文学史的审美标准?或许正如他们在当时由王干倡议发起的一次讨论中所表达的那样: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一套审美标准。对于文学而言的确如此,对于不关心文学史的他们而言(韩东在后来的谈话中对这一点似乎发生了些许变化),这也是必然走向的一个结论。然而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是否真的具有某种根本的指引性?这仍然是如今的我们所不断质疑的。
无论如何,评论与关注是必须的,不能因为他们反传统、反体制就搁置忽视、闭口不谈。多年来,在一种不无刻意漠视里,我们不难看到与历史相似的影子——五十到七十年代的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鸳蝴和海派。历史已经给予我们一种惨痛的教训,但相似的历史逻辑却得到了继承(尽管它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正如它通过言说方式侵入一代人的思维方式那样狡猾而隐秘),只不过主体和条件都发生了变化:权威从以体制为代表的意识形态转向以学院派批评界为代表的新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仍有难解难分的关联)。当话语权发生转向,历史再度重演,这才更值得我们反思,或许真如朱文所感愤抗议的那样:“人情世故的东西太多了,它已经腐蚀到汉语文学的中枢神经。”
要声明的一点是,我无意为这批作家“翻案”,也不是偏要旧事重提;只是,在考察九十年代文学环境以及追踪他们的人生轨迹的过程中,一种明显的由历史促生的偏颇在我的面前显露出来,我不能不去正视它。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断裂”并没有阻碍他们的发表,甚至在“断裂”当年与其后两年间,他们的作品发表量急速增长。表面上,他们确实获利,按韩东的话说就是“写出来了”,但当我们迫不及待指认他们为“作家”的时候,是否又是操之过急?与这批参加断裂活动的群体十分熟悉的张生在后来的谈论中指出:“或许我们这批人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影响的产物。”对于这种影响,他指出村上春树的写作以及60年代美国文化的转入。这一点自然不容忽视,正如他提到的自我怀疑,那么相较他还不如的一批人,写了一本书、十几万字的中短篇,就算是作家了吗?九十年代末期刊出版的畸形业态和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蓬勃兴盛带来的正是一种无节制的发展态势。或许,经由编辑之手发表出的作品确有某些过人之处,但很难承认其中完全不存在炒作的嫌疑——毕竟“断裂”可谓文坛世纪末最热闹的事件之一,对文学轰动效应的追逐已经成为陷入泥沼的文学期刊所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事实上,除了朱文、韩东等人,大多数“作家”的写作仍存在一种本质上的重复倾向,但所谓的“个人”一旦泛滥开来,“个人”的潮涌也终将汇聚成团,将原本的“个人”转化为另一种“共名”(借用陈思和的“共名”概念,只不过此处只是一个局部的“共名”)。
前边已经说过,基于道德标准的评判是值得怀疑的,而实际上也确实没能形成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审美标准,更何况已有的场域准入者的审美标准也受到经济场和政治场的复杂侵蚀而难以坚持某种本应具有的独立姿态(其实,当代文学并不存在所谓的“独立姿态”,“看不见的手”一直存在,只不过施加影响的手段、方式以及程度都处于动态调整之中罢了),那么“断裂者”的合法性(文学史意义上的)就是可疑的。我在这里又重复了一次自己的基本判断,但是——是的,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但是”,这种写作已经出现,按照闫老师的看法,存在本身就已经赋予了它们合法性,当作客观事实看待的情况下,我们又过于忽略了它们产生的影响。
在备忘中,韩东指出,“和我们的写作实践有比照关系是早期的‘今天’、‘他们’的民间立场,真实的王小波,不为人知的胡宽、于小韦,不幸的食指,以及天才的马原。”这份名单构建起另一条可以追溯的线索——至少王小波可以被追溯。王小波的创作与他的死亡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的遭遇与“断裂”是相似的,它们都被“歪曲”,都变成一种与出发点相悖的“表演”,被卷入商业话语的漩涡之中难以自证。但实际上,王小波作为韩少功、王安忆的同代人,他的知青书写显得颇具异端色彩,那是一种个人的言说方式,而不是群情激愤的理想年代,不是一种美好岁月的缅怀,个人——被提溜出来,以性为手段,以戏仿、讽刺、嘲弄为方式。朱文韩东与之遥相呼应,而在他们之后——伊沙、沈浩波主导的“下半身”以更加极端的方式宣告个人性。可以说,“断裂”的影响被小觑了——它似乎成为一道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分水岭,宣告一种独立于体制、秩序之外的纯粹个体的写作是可能的。这里隐含着一种错位的关系,即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九十年代文学更多与市场纠结(无论是新历史转向、先锋作家“触电”、《废都》事件还是“布老虎丛书”),但“断裂”的对象却盯紧的是制度与文坛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断裂者”是一群不合时宜的人,是“错位者”,他们宣告断裂,但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断裂”的一代。当时间越过千年的大门,更年轻的一代从一开始就不考虑体制、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才是真正的“断裂者”。基于此,我们回看过去,才更能理解韩石山那份当时少有的对“断裂”的正面评价:“不必推测他们将来的成就了,他们现在做的这些,不是我们这一代敢做的,甚至不是我们这一代敢想的,这就足够了。”因而,“断裂”是个体时代的产物也促使文学大踏步迈入个体时代,它的“功绩”并没有被恰当地估量,即便不是“开拓之功”,但行为本身带来的破坏性也足称得上是“推倒高墙的最后一脚”。它所开辟的新的书写领域至今仍在当下的写作中不断涌现着,这种“功绩”应当被追认,也应当被重新提出与考虑。
然而,我们无法欢呼,也不能欢呼。正如吴晨俊在当时已经表现出的忧虑:破坏总是容易的,但更关键的却是建构。“个体写作”通过“断裂”的助攻成功在写作者那里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并且愈发形成不可阻挡的势头。在“写作只是个人之事,它不对任何其它东西负责”的名号下,意义被悬置,文学的教育作用被放逐,延续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精神”彻底陷入尴尬的境地,就像“断裂作家”对“人文精神大讨论”的鄙夷和不屑,这种破坏的力量在当代社会思想文化中所向披靡。不过,事实与真相永远是复杂的,当它以为自己处于无可争辩的“独立”状态时,却未能发现自己早已被政治与经济“捕获”,间接中成为它们更好用的“工具”,其结果最浅显的表现在一些语词性质上的变动(“公知”,“文青”等等),更深则表现在当下精神文明的诸多问题之中。
破坏远比建立更加简单,这也是我阅读《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时的感受。或许正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西方当代理论的解构性质带来的并不一定都是好事,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因此要转向所谓的且至今尚无确论的“传统”并形成非此即彼的基于某种可笑的“民族主义”的逆反观念。在我看来,这种观念较之前者更加可疑。
从断裂开始,时间又匆匆走过二十三个年头,确实堪称“物是人非”,“忽视”带来的结果变得加清晰可见:同属当代,历史却已然破碎,难以补全。当代文学生产传播体制在九十年代末经历崩溃重建,在之后的尽十年内几乎原地踏步,或许最近几年才开始获得初步进展,只不过一切都不好说,对于那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以为它悄然退场,实则它从未远去。或许,对于未来,我们难以展望(即便可以,但仍旧不堪一击),能做的只有处理好当下。
- 0
-
赞助
.png) 支付宝
支付宝
-nogc.png) 微信
微信
-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