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者笔下外国人眼中的日本人 ——续说横光利一《上海》中的人物表象
编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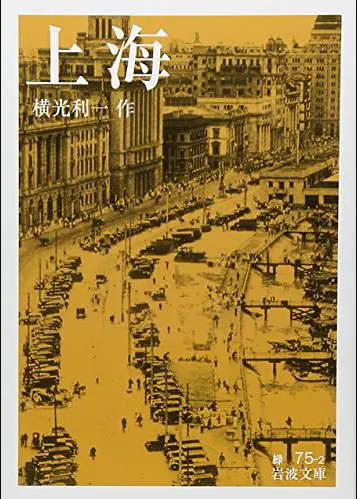
摘要:
本文对李征教授未能论述的“日本人在外国人眼中的表象”加以说明。小说采用不定内聚焦型叙述视角,在涉及政治经济等宏观国际问题时常常出现“虚拟的在场者”,作为日本人的“虚拟的在场者”承接了部分视角,因而外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实际上带有日本人自我臆想的特点,这同样反映出日本人对外国人的态度。中国人、印度人眼中的日本人形象多带有侵略扩张色彩,日本人对这二者有异常密切的关注并持否定批判态度。欧美人对日本人更多是轻蔑和不屑,日本人对欧美人亦带有复杂矛盾的病态心理,后者拒绝接纳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上海》 叙述视角 叙述声音 人物表象
时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的李征教授于201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身体的表现与小说的政治学——横光利一<上海>中的外国人表象》的论文。在文章中他以“小说中日本人看待租界中其他国籍的居留者的方式”(即所谓的“外国人表象”)作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横光这部作品的连载版本与定本中对非日籍人物书写的改动情况,勾勒出其背后所显示出的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以前两者为基础的亚洲主义的文化与政治观念。然而正如他在文末所说到的那样,这篇文章并未能完全论述涉及到“人物表象”这一概念的所有问题,其中对于“日本人的欧美表象”和“日本人在外国人眼中的表象”尚未能加以述说。基于这一情况,在初步了解当下中国学界对横光《上海》这部作品的研究现状后,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接着说”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对其他问题“照着说”更具有学术意义。尽管身为初学者,但笔者亦希望尽己之力来为李征教授所未能得闲说明的“外国人眼中的日本人”这一问题做出一定程度的解读。
一、理论依据
在进入对文本的具体阐述之前需要对标题中涉及到的几个概念进行解释,这是本文的基本立足点之一。
“人物表象”即经过语言的描写、刻画和塑造所形成的人物形象,而“外国人眼中的日本人表象”不仅包括了小说中所出现的印度人和欧美人对日本人的看法,而且涵纳了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而要明确所谓的“眼中”则涉及到“视角”和“声音”这一对叙事学概念。
热奈特在试图区分小说的观察者与叙述者时曾指出在许多理论家那里都出现了“在我所称作的语气和语态之间的令人遗憾的混淆,即谁是叙事文中观察者的问题和完全不同的谁是叙述者的问题之间的混淆,或更直截了当地说,谁看(感知)与谁讲之间的混淆”。[1]这实际上已经将叙事过程中的人员分工进行了更为细致地划分。基于这一情况,“视角”这一范畴被确认并用于研究“谁看”即谁在观察故事,“声音”则用于研究“谁说”的问题。而在许多作品中,二者的来源却并非完全一致:“视角是人物的,声音则是叙述者的,叙述者只是转述和解释人物(包括过去的自己)看到和想到的东西,双方呈分离状态。这种现象无论是在讲关于他人的故事还是在讲关于自己的或包括自己在内的故事中都存在。”[2]正因如此,由“视角”和 “声音”牵扯到了叙事文本中的人物和叙述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横光利一的《上海》中,从整体上看,叙述人和人物并不完全一致,小说在绝大多数场合采用的是热奈特所谓的不定内聚焦型叙事视角,在这种视角下,“它完全凭借一个或几个人物(主人公或见证人)的感官去看、去听,只转述这个人物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而对其他人物则像旁观者那样,仅凭接触去猜度,臆测其思想感情。”[3]然而在一部分场合中(这些场合正是本文将着力关注的),由于这些对话更多是围绕着一个观点所展开的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的讨论,因而在叙述通过这一视角所看到的景象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发出“声音”的外在观看者以自己的视角取代原有视角的现象,在这时,叙述者不再完全附身于对话者(即人物),他开始站在一个类似读者所处的位置,并且成为一个独立于对话双方之外且默默旁观着整个对话进程的一个“虚拟的在场者”。但正如所有的叙述者都有其特定的身份,《上海》中这一“虚拟的在场者”(亦即叙述者)亦是以日本人这一身份而存在的,这令小说获得其特殊性。
笔者在标题中还用到了“外国人”这一概念,从表面上看,这里由日本人作为参照系似乎与故事发生的地点——中国上海有所矛盾,但实际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无论是小说的真实作者还是小说的叙述者均是站在日本人这一视角/出发点下进行创作与叙述的。这就构成了刚刚所说的特殊情况,即当我们在探讨“外国人眼中的日本表象”时,这些“外国人”的观点和看法其实是由潜藏着的“日本”视线所建构起来的;这就为此处“日本人表象”的塑造提供了一种双向性,即“外国人眼中的日本人表象”实际上是日本人臆想中的外国人对自身的看法,这种臆想虽然很可能有其客观依据,但从根本上仍旧无法完全代表真正意义上的“外国人”的真实声音,因而它也就显示出主观性,亦在无意中透露出这个“虚拟的在场者”对这些“外国人”的某种看法。
此外,同样需要明确的是出现上述情况的具体场合。在小说中,“外国人眼中的日本人表象”仅仅在小说语言描写中得到体现,而且只有在双方所谈论的对象上升到族群这一层面时,“日本人”才能作为一个被拿来讨论的集体,人物的声音也才会转变为叙述者的声音。在这些场合中,谈话双方所论及的问题往往是与当时上海、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等内容有关的重大问题。而除此之外的其它涉及到日本人同外国人的交流,则更多地体现为平常式的个体对个体的态度和看法,它们就并非本文所主要讨论的内容。
至此,在明确了本文在论述时的几个出发点之后,笔者将进入对具体文本的解读和阐述。
二、日本叙述者视角下中国人、印度人眼中的日本人
与作为背景出现的次要人物有所不同,横光利一在《上海》中塑造了两位有着截然差异的中国角色——民族资产阶级钱石山与作为革命发起者之一的芳秋兰。饶有意味的是,在两人出现的场景中,与他们产生交流的对象正分别是甲谷和参木这两个日本人,因而通过这两个中国人的眼光和谈论,小说中日本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就得到了展现。
我们首先关注芳秋兰与参木的对话。在小说中,高重所在的纺织厂在夜里上班的时间被暴徒突然袭击,在一片混乱中,主人公参木救下了被四处逃窜的人群绊倒的芳秋兰,翌日早晨,秋兰为答谢参木邀请他到一家中餐馆吃饭,在刚刚坐定时发生了这次对话。谈话主要涉及到中日问题以及二人对于革命的不同看法。芳秋兰认为日本的东洋主义是为其资产阶级服务的,它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帮凶,而中国人的革命则并不针对其无产阶级,为了解放中国以及日本的无产阶级就必须对日本资产阶级侵略势力加以反抗。从根本上说,芳秋兰对日本的态度完全立足于阶级立场,她认为日本的资产阶级有着明显的侵略扩张意图,自己所倡导的革命正是为了摆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被她视为东洋主义者的参木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日本侵略势力的帮凶。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革命者眼中,日本显露出扩张性和危险性这两个特质,但这主要来自日本资产阶级,而日本的无产阶级则被视为无辜者。可以说,芳秋兰的这一观点同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在这里,日本人被建构为一个邪恶的势力,这合乎当时的具体历史语境。但重要的问题在于,在芳秋兰做出这一论述的过程中,作为日本资产阶级代表的参木对其所有表态都做出了有力的反驳。在他看来,自己对日本的维护只是出于最基本的民族国家认同感,而芳秋兰所谓的革命对日本无产阶级而言也是一种外在的欺压,日本乃至西方列强的资本输入有助于中国赶上当时的世界各国。这无疑是参木完全从自身国家角度出发的一种观点,看似合理但实则隐藏着殖民侵略的意涵。
同样的,在这次对话中,“视角”的发出者和“声音”的接受者正是此前所提到的“虚拟的在场者”,他在这里从参木的身体里脱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个体观察着整场对话,因而对话双方的语气、心理状态实际上成为由他所建构出来的内容,这些“声音”和“视角”的背后也因此显示出他的隐含观点。在整场对话中,无论是那句“我们不愿意让日本人总是看到我们的弱点”[4]还是对话中“秋兰就像被这突如其来的理论给卡住了那样,眼睛炯炯发光”[5]的描写,都显示出芳秋兰在面对日本人时有着高度的自尊与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然而与此同时,叙述者在双方交谈的过程中对芳秋兰的塑造却带给读者以一种略占下风的感受,这同她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笔者认为,此处身为虚无主义者的参木能够轻易将“革命领袖”辩驳得有些难以自圆其说,这一设置正反映出身为日本人的“虚拟的在场者”对中国人的看法,即虽然看到了中国人内心的自尊意识,但仍旧否认其反抗压迫与暴力革命的做法,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人通过革命推翻外来侵略势力这一行为的合理性的颠覆,从根本上反映出当时日本人的殖民侵略心理。
而在另一场对话中,作为民族资本家的钱石山成为小说中第二个发表对日本及日本人看法的中国人,他同甲谷的谈话从经济角度出发最终落脚到政治观点上。在谈话的伊始,钱石山在恭维甲谷的同时暗含着某种讥讽:“我听说贵国在那里(新加坡)发了大财。”“……最近贵国很活跃嘛。”[6]这些都是象征性的恭维,但其语调始终显露出一种高人一等的调侃意味,而随即话锋一转又以一种不经意间随口提到式的轻佻态度指出“贵国似乎在为中国的排斥日货而大伤脑筋。……啊,对了,今天又有四家日本纺织厂因闹罢工而垮台了。”[7]则带有明显的故意刺激甲谷的成分,显示出他对日本的轻蔑。而接下来面对甲谷的迅速反击,他又“露出猛然被刺中痛楚那样一种狼狈相来”[8],收起了自己的锋芒,开始表现得“谦逊”。
仅从有关生意方面的谈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资本家的钱氏对日本在东亚地区产业布局状况的重视,这或许是出于二者是竞争对手关系的缘故,但在接下来的政治交流中他却又明确澄清自己“一贯主张亲日是头等重要的”[9],这就显示出日本侵华势力在当时中国的权势阶层那里有着独特的存在地位。然而从根本上讲,这种重视是钱石山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非其它,因此在甲谷开始对自己的政治观点发表长篇大论时,“钱石山也许看出阿柳对两个人的谈话感到索然乏味了吧,他像要打断甲谷话题一样”,“左顾右盼地吸吮着早已没有味道的茶水”,快人快语地敷衍起来。[10]
可以说,在整场对话中钱石山对于甲谷的态度基本是应付和敷衍的,这表现出他对日本人仍旧保有骨子里的轻蔑以及对自己高人一等的自矜,尽管这种妄自尊大的态度在谈判的过程中被惊异打断了几次,但并未能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而相较于政治问题——尽管他也对甲谷所论及的有关地区局势的问题有所了解,但很明显,他的关注点更多地聚焦于经济、女人还有享乐这些方面,他所认定的行事基点也全都是出于符合自身利益的需要,这是他对甲谷长篇大论不感兴趣的根本原因,同时反映出他内心中对国家民族观念的淡漠。
结合上述情况,“虚拟的在场者”所听到的和看到的钱石山就不仅仅是甲谷所直接感受到的那样,充满了颓废奢靡的气质且带有可鄙的窥探欲,他的身上还被赋予了某种过来人般的、装作看透了一般的心态,因而在面对外国人时,他也并不显露出低人一等的感觉,反而自我感觉良好并带有很强的进攻性——在谈话的开始他便自认为已经“洞察出日本的要害”,一开口就直接点明了日本时下的窘迫并为此“妄自尊大地笑了起来”,所以甲谷听罢后“所考虑的已不再是向他推销木材而是指斥中国人的弱点”——这种对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局势有着了如指掌的把握的设计,以及言谈所显示出的一种“评点”式的态度无疑丰富了整个人物的形象。但即便如此,“虚拟的在场者”最终仍将自己对他的评价定位为消极和无法认同的。钱石山不仅在面对甲谷激情的论说时多次语焉不详,而且在为了个人利益这一根本出发点而不断腾挪周旋于革命者和日本人之间以期获利,这些举动无疑与芳秋兰等人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在这一点上“虚拟的在场者”同小说人物甲谷一样,都认为钱石山是可鄙且不堪的,而由于钱石山所带有的典型性特点,这种看法的针对对象可以更进一步延伸拓展到当时中国的整个权贵阶层。
行文至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引入小说的真实作者与叙述者(亦即此处的“虚拟的在场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笔者认同巴尔特的言论,“叙述者和人物主要是‘纸上的生命’。一部叙事作品的(实际的)作者绝对不可能与这部叙事作品的叙述者混为一谈。”[11]但即便如此,笔者仍旧认为叙述者无法完全脱离作者而存在。尽管叙述本身有其内在所要遵循的理路,但缺乏了作者这一外在主体,创作过程中思维的活动便无法完全进行下去,因而叙述者和被创制出的人物身上所显露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真实作者某些观念的内在反映;更何况《上海》是一部被视为完全由横光利一本人观念所组构而成的作品[12],人物所发表的议论性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横光本人的观点。正因如此,笔者在以上论述过程中所提到的“中国人眼中的日本人”与“虚拟的在场者眼中的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可视为是横光对当时日本自身的问题、日本与中国的问题以及革命、马克思主义等问题的看法,而正是这些看法体现出了他立足于狭隘自私的民族主义情感而非世界主义的态度,因而一些观点也就带有一种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意图和种族歧视观念打掩护的色彩。可以说,横光在《上海》中所体现出的观念正同诸多论述者所认定的一样——是消极且不可取的。这一点在小说中印度人的眼中也同样得到了展现。
小说所涉及到的唯一非背景式的印度人形象——阿利姆被定位为一位曾久居东京,经营珠宝,带有“亚细亚主义”倾向,支持印度独立但却畏惧共产主义运动的印度商人。他与日本建筑师山口的对话体现出他对山口所代表的一类日本人的态度。
在他看来,山口所强调且热切宣传的日本军国主义必然会同苏联所强调的共产主义相冲突,而面对家乡的紧张局势以及面前喋喋不休的山口,他不留情面地斥言道:“你看什么都觉得像共产党。你那么害怕共产党,那亚细亚主义也就完蛋了。”[13]从这里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共产主义势力的担心和异常关注,这与高重一早就把握了芳秋兰的底细但又迟迟不动手这一情节相吻合,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当时作者对共产主义的矛盾态度[14](纵观笔者所收集到的材料,所有研究者都无一例外地将小说中人物的论说视为作者自己的看法,其中,横光对芳秋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书写就反映出他对之的态度。 诸多论者都指出横光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矛盾且复杂的。一方面,对现实不满以及改变个人生活现状的诉求使得他对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斗争有所向往,但另一方面他又害怕革命会摧毁他个人甚至祖国(这是针对中国的革命而言的)既得的一切。童晓薇认为《上海》中对芳秋兰和阿杉这两个人物的设置就反映出横光的这种摇摆不定:在她看来,象征着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芳秋兰是他深陷囹圄时所希望能来救他的人,而阿杉则似乎可以说是他的旧我、他的传统的象征符号,在小说中前者成为最能吸引他的异性,而后者则是他所选择的最终归宿:“如果那天我没有碰到芳秋兰,我一定就去追阿杉了”。王天慧则将之归因于横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足: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解得并不清晰,甚至很有些主观片面的味道,但他并非反马克思主义者,只是认为它具有较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而已。”由此出发,他指出只要人类本能欲望存在,为利益而进行的争斗就不可能停止,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扬的“阶级”、“革命”只会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剧烈、更加血腥。[王天慧69-70;童晓薇118]杨金玲则从芳秋兰人物设定不符合中共党员的实际情况这一点切入,提出横光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足,这反映在芳秋兰的身上成为她的某种性格缺陷,这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既向往又抗拒,既渴望又排斥。”的态度。同时,她又补充了小说在连载时的材料:“最初的杂志版本中,有一些参木赞同芳秋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描写,但在最终的定本《上海》中,这些描写被大量删除。”并由此认为“横光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出越来越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杨金玲III]宋隽由参木同芳秋兰的辩论入手,指出芳秋兰无力反驳参木的反对阶级革命的观点,并认为这表现出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否定,而芳秋兰最终的结局则体现了作者“无产阶级斗争对于改变中国的现状并无作用,只会造成无谓的牺牲”的态度。[宋隽14])。而在另一方面,小说叙述人通过语言描写为阿利姆赋予了热心关怀政治,虽然内心有所困窘但仍试图强装镇定的特点,这与钱石山有着相似之处。值得关注的是,钱石山与阿利姆身上所体现出的这种表面上的游刃有余又都被日本人一语中的地加以揭穿:在小说中,山口经过一次又一次地逼近和追问迫使阿利姆怀着满心的忧虑解答了当时印度所处的艰难环境,而正是这种对“现实”的书写又恰好反映出当时的日本对东亚的诸多国家采取了密切关注的态度,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小说中所谓的“亚细亚主义”的根本意涵——即蓄谋已久的侵略扩张意图;在另一个层面上,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种书写亦体现出当时的日本国内确实有逐渐被“只有军国主义、亚细亚主义才能拯救整个亚洲”这一思想所占据的倾向,因而从客观上也揭示出一种殖民侵略倾向。
三、日本叙述者视角下欧美人眼中的日本人
如果将中国人眼中的日本人和印度人眼中的日本人形象视为一个序列,那么在《上海》中,日本叙述者视角下欧美人眼中的日本人形象则由于其特殊性而应被拿来进行单独分析。
涉及到相关内容的部分集中在宫子在穆斯林舞厅与几个欧美男性交谈这一场景中。“在宫子跳舞的舞厅,一群缠绕着宫子的外国人在谈论日本纺织公司的罢工。宫子跳过一曲之后便走到早已有了几分醉意的外国人桌子旁边,侧耳听着一个叫费杰尔的德国男人的谈话。”[15]从这里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叙述者的“视角”原本是基于宫子的,但随后当宫子也开始进入谈话,对人群的观察角度就转换到了“虚拟的在场者”身上。
白人男子费杰尔将工人的罢工归因于日本管理者,在他看来,“不尊敬外国人”的管理者受到中国工人的反抗完全是自作自受,但在结束自己的话语时却又留下了耐人寻味的表述:“我们倒是为此而感到幸福。不,我们将与各位一起为宫子小姐而悲伤。”[16]弗洛伊德指出每个人的失误动作背后都具有一定的可探讨价值,它们通常反映出施动者内心的真正想法。基于这一观点,在“虚拟的在场者”的盯视下,费杰尔先生话锋的突转不仅显示出他为日本厂家受挫而沾沾自喜的小人心态,而且体现出他对宫子过于夸张地恭维以期换取其好感的逐利心理,在这里,给人以莫名奇妙感觉的后者正是为了掩盖表现了内心真实想法的前者,因而费杰尔这一形象在叙述者的“声音”中体现出虚伪的特质。
现在让我们回到他对日本人的看法上来。从总体上讲,他的话语中显示出对日本人的轻蔑和嘲弄,这与他拜倒在宫子石榴裙下的做法却构成了极具冲突感的对立,这一现象似乎与参木等人拜倒在芳秋兰裙下有着某种相似性,然而实际上却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奚皓晖认为小说中的女性都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其中,参木与作为“现代女性”(modern woman)的宫子的关系代表着虚无主义的情欲之爱,而同芳秋兰的情感实际上被视为带有前现代意味的古典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之爱。[17]在这个意义上,宫子这一形象被视为现代人“情欲”的化身。尽管小说中并未能明确地指出,但费杰尔对于宫子的追求亦可视为是对情欲的追求,正因如此,日本女性在欧美男子的眼中并非他物,而只是满足自身情欲的“工具”,这正与费杰尔话语中的轻蔑意味相一致。因而可以说,在小说中欧美人对日本人的看法仍旧是轻蔑和鄙弃的,这一点在后来甲谷逃命时美国大兵无所作为但却露出微笑这一情节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然而饶有意味的是,作者又刻意地为我们展现出参木出现在这群白人男性面前的情况。面对突然出现的参木,两个争风吃醋的白人男性感受到“心慌意乱”,这种欧美人被日本人比下去的现实与他们视日本女性为满足情欲的工具的现象带有鲜明的讽刺意味,与这种矛盾性相关的是这些白人在宫子“视角”下所展露出的形象。费杰尔同另一个白人男子克里巴在宫子面前对吊灯所属厂家的争执给人一种极为可笑且幼稚的感觉,这也正是宫子眼中的两个白人男子的形象,换句话说,作为“情欲”代表者的宫子并没有放任自己沦为被他人所取用的“玩具”,相反,她自己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并且乐意看到诸多外国男子在自己面前互相“争宠”。但饶有意味的是,除了参木之外,被宫子看上另一个日本男性甲谷却也长着一副类似欧美男性的英俊样貌,结合她“只同外国人交往”的处事原则,笔者认为宫子内心还是对欧美男性有着强烈的渴望,这正反映出欧美人在当时日本人眼中的独特地位。
在后殖民文学文本中有一种明显的故事类型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即代表先进(殖民)国家的男性被落后(被殖民)国家的女性所吸引而构成一段爱情故事。在《上海》中,芳秋兰对参木的浓厚吸引力无疑正契合了这一故事类型,然而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宫子与甲谷及诸多外国男性的关系与此处的某种若隐若现的关联。如果我们同样将宫子和他身边的男性加以抽象概括,那么前者则可视为较先进国家中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后者可被视为较先进国家中带有更先进国家血统的现代男性,从这种抽象中可以发现宫子对外国男性的态度似乎正可以与参木对芳秋兰的感情形成某种隐微地且富有寓意的对应,而与前者那种因相似的故事类型而体现出的殖民侵略色彩所不同的是,后者实际上可被视为是较先进国家希望委身于更先进国家这一事实[18],从本质上讲,这所体现的仍旧是一种民族国家层面的自卑心理。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小说中日本人眼中的西方人形象实际上是十分复杂的:他们一方面被赋予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对他们的书写与刻画又带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轻蔑态度,这正反映出当时日本人在面对欧美人时内心中的一种自卑又倨傲的矛盾心态。李征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小说显示出对白俄的蔑视可被视为一种倒错的优越意识:“尽管身为黄色人种,但日本一直在谋求跻身欧美列强,在欧美面前的强烈自卑意识,因日俄一战发生了逆转。自卑变成了优越意识。尽管这种优越意识仅限于白俄身上,但恍惚中,却幻化为对整个白人世界的胜利。”正因如此,“小说中日本对欧美的框架,正像一种集体心理装置,把作为黄种人被一直蔑视的日本人的民族自卑感、劣等意识,以对白俄的蔑视这种倒错形式反施于欧美。”[19]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小说所表现出的日本人对欧美人的看法(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看法还是笔者所提出的日本叙述者视角下的看法均是如此)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病态的心理,它从根本上反映出的是当时的日本在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时的一种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且足够强大但却迟迟未能得到期待已久的认可的心态,而正是由于这种未能被认可,促使日本人更进一步地思考如何才能超越西方,走到世界的中央。因而可以认为,这种观念成为推动当时的日本在所谓东洋主义、亚细亚主义等观念影响下最终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对于日本叙述者视角下外国人眼中的日本人表象的分析,我们最终所得到的实际上仍旧是那个老生常谈的结论。在横光的笔下,上海甚至中国无疑成为一个东方主义意义上的“他者”,在这里,近代日本在作为东方的“西方”的同时又同时是西方社会眼中的“东方”,因而日本叙述者视角下外国人眼中的日本人就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气质。在面对比它落后的东亚国家时,它通过特定的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表现出一种自矜的优越感,但在面对欧美人时,这种优越感由于对方的不予认同转而与一直存在的自卑心理混同在一起,共同构成一种病态的心理。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两种心理最终所导向的结果均是使近代日本走上对外扩张与殖民侵略的道路。可以说,在这样一种话语的建构下,政治态度依旧是小说所要表达的核心内容,正因如此,李征先生在他那篇文章中所言的“外国人表象无形中折射了一九二零年代至一九三零年代期间日本人的国际认知”在这里仍旧适用,这也成为《上海》这部小说至今仍然值得研究者不断翻阅并试图阐释的根本原因之一。
脚 注
[1]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
[2]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1.
[3]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7.
[4] [日]横光利一著,卞铁坚译.寝园[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77.
[5] [日]横光利一著,卞铁坚译.寝园[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81.
[6] [日]横光利一著,卞铁坚译.寝园[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90.
[7] 同上
[8] [日]横光利一著,卞铁坚译.寝园[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91.
[9] [日]横光利一著,卞铁坚译.寝园[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93.
[10] [日]横光利一著,卞铁坚译.寝园[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95.
[11]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7.
[12] 这一问题已被国内诸多研究者视为定论。
[13] [日]横光利一著,卞铁坚译.寝园[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112-113.
[14] 此处所涉及到的文献分别如下:童晓薇.横光利一的《上海》之行[J].中国比较文学,2007,3:102-118;王天慧.横光利一文学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1,69-70;杨金玲.异乡的彷徨——论横光利一之《上海》[D].长春:吉林大学,2011;宋隽.横光利一笔下的上海形象[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3,14.
[15] [日]横光利一著,卞铁坚译.寝园[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100.
[16] 同上
[17] 奚皓晖.现代性论域中的横光利一[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7,41.
[18] 在小说中,与宫子来往的全都是外国人,绝大多数都是欧美人,即便是甲谷和参木也都是因为“长得像外国人”才被宫子所关注。见[日]横光利一著,卞铁坚译.寝园[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41-42、66.
[19] 李征.身体的表现与小说的政治学——横光利一《上海》中的外国人表象[A].谭晶华,李征,魏大海.日本文学研究 多元视点与理论深化 日本文学研究会延边大学十二届年会论文集[C].青岛:青岛出版社,2012:12.
参 考 文 献
【1】[日]横光利一著,卞铁坚译.寝园[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2】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7.
【3】李征.身体的表现与小说的政治学——横光利一《上海》中的外国人表象[A].谭晶华,李征,魏大海.日本文学研究 多元视点与理论深化 日本文学研究会延边大学十二届年会论文集[C].青岛:青岛出版社,2012:8-25.
【4】奚皓晖.现代性论域中的横光利一[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7.
【5】李圣晨.横光利一笔下的上海形象研究述评——以长篇小说《上海》中的形象为例[Z].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2019-12-4.
- 0
-
赞助
.png) 支付宝
支付宝
-nogc.png) 微信
微信
-
分享